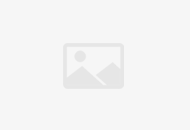《宋史.苏轼传》的翻译
苏轼,字子瞻,眉州眉山人.生十年,父洵游学四方,母程氏亲授以书,闻古今成败,辄能语其要.程氏读东汉《范滂传》,慨然太息,轼请曰:“轼若为滂,母许之否乎?”程氏曰:“汝能为滂,吾顾不能为滂母邪?”
【译】苏轼字叫子瞻,是眉州眉山人.十岁时,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,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,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,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.程氏读东汉《范滂传》,很有感慨,苏轼问道:“我如果做范滂,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?”程氏说:“你能做范滂,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?”
比冠,博通经史,属文日数千言,好贾谊、陆贽书.既而读《庄子》,叹曰:“吾昔有见,口未能言,今见是书,得吾心矣.”嘉祐二年,试礼部.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,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,得轼《刑赏忠厚论》,惊喜,欲擢冠多士,犹疑其客曾巩所为,但置第二;复以《春秋》对义居第一,殿试中乙科.后以书见修,修语梅圣俞曰:“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.”闻者始哗不厌,久乃信服.
【译】 到二十岁时,就精通经传历史,每天写文章几千字,喜欢贾谊、陆贽的书.不久读《庄子》,感叹说:“我从前有的见解,嘴里不能说出,现在看到这本书,说到我心里了.” 嘉祐二年,参加礼部考试.当时文章晦涩怪异的弊习很重,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,见到苏轼《刑赏忠厚论》,很惊喜,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,但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写的,便放在了第二名;又以《春秋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,殿试中乙科.后来凭推荐信谒见欧阳修,欧阳修对梅圣俞说:“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.”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,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.
丁母忧.五年,调福昌主簿.欧阳修以才识兼茂,荐之秘阁.试六论,旧不起草,以故文多不工.轼始具草,文义粲然.复对制策,入三等.自宋初以来,制策入三等,惟吴育与轼而已.
【译】服母丧.嘉祐五年,调任福昌主簿.欧阳修因他才能识见都好,举荐他进秘阁.考试作策论六篇,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,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.苏轼开始起草,文理就很清晰.又笔答制策,被列入第三等.从宋初以来,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,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.
除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叛官.关中自元昊叛,民贫役重,岐下岁输南山木筏,自渭入河,经砥柱之险,衙吏踵破家.轼访其利害,为修衙规,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,自是害减半.
【译】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.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,百姓贫困差役繁重,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,从渭河进入黄河,经过砥柱的险处,衙前役人相继破产.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,为他们修订衙规,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,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.
治平二年,入判登闻鼓院.英宗自藩邸闻其名,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,知制诰.宰相韩琦曰:“轼之才,远大器也,他日自当为天下用.要在朝廷培养之,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,皆欲朝廷进用,然后取而用之,则人人无复异辞矣.今骤用之,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,适足以累之也.”英宗曰:“且与修注如何?”琦曰:“记注与制诰为邻,未可遽授.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,且请召试.”英宗曰:“试之未知其能否,如轼有不能邪?”琦犹不可,及试二论,复入三等,得直史馆.轼闻琦语,曰:“公可谓爱人以德矣.” 会洵卒,赙以金帛,辞之,求赠一官,于是赠光禄丞.洵将终,以兄太白早亡,子孙未立,妹嫁杜氏,卒未葬,属轼.轼既除丧,即葬姑.后官可荫,推与太白曾孙彭.
【译】 治平二年,入朝判登闻鼓院.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,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,管理制诰之事.宰相韩琦说:“苏轼的才能,远大杰出,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.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,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,都想要朝廷使用他,然后召来加以重用,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.现在突然重用他,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,恰恰足以使他受到牵累.”英宗说:“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?”韩琦说:“记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,不可马上授予.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,而且请召来考试.”英宗说:“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,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?”韩琦还是不同意,到试了两篇论,又列入三等,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.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,说:“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.” 适逢苏洵去世,朝廷赐给他金帛,苏轼推辞了,要求赠父亲一个官职,于是赠光禄丞.苏洵将死,因哥哥太白早死,子孙没有成人,妹妹嫁给杜氏,死了还未下葬,嘱咐苏轼.苏轼服丧期满后,就马上安葬了姑母.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,就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. 熙宁二年,还朝.王安石执政,素恶其议论异己,以判官告院.四年,安石欲变科举、兴学校,诏两制、三馆议.轼上议曰:得人之道,在于知人;知人之法,在于责实.使君相有知人之明,朝廷有责实之政,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,而况于学校贡举乎?虽因今之法,臣以为有余.使君相不知人,朝廷不责实,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,而况学校贡举乎?虽复古之制,臣以为不足.夫时有可否,物有废兴,方其所安,虽暴君不能废,及其既厌,虽圣人不能复.故风俗之变,法制随之,譬如江河之徙移,强而复之,则难为力.庆历固尝立学矣,至于今日,惟有空名仅存.今将变今之礼,易今之俗,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,敛民财以食游士.百里之内,置官立师,狱讼听于是,军旅谋于是,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,则无乃徒为纷乱,以患苦天下邪?若乃无大更革,而望有益于时,则与庆历之际何异?故臣谓今之学校,特可因仍旧制,使先王之旧物,不废于吾世足矣.至于贡举之法,行之百年,治乱盛衰,初不由此.陛下视祖宗之世,贡举之法,与今为孰精?言语文章,与今为孰优?所得人才,与今为孰多?天下之事,与今为孰办?较此四者之长短,其议决矣.
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: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,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,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,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,此皆知其一,不知其二者也.愿陛下留意于远者、大者,区区之法何预焉.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.夫性命之说,自子贡不得闻,而今之学者,耻不言性命,读其文,浩然无当而不可穷;观其貌,超然无着而不可挹,此岂真能然哉!盖中人之性,安于放而乐于诞耳.陛下亦安用之?
【译】熙宁二年,苏轼回到朝廷.王安石执政,向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,任命他做判官告院.熙宁四年,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、兴办学校,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,史馆、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商议.苏轼上折发表议论说:
求得人才的道路,在于了解人;了解人的方法,在于注重实际.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,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,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,何况学校和科举呢?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,我以为人才还有余.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,朝廷不求实,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,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?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,我以为还是不够.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,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,正是合适的时候,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,等到不再适用时,即使时圣人也无法恢复.所以风俗的变化,法律制度就跟着改变,好像江河的改道,强求复旧,就难以奏效了.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,到了今天,仅存空名.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,更改当今的风俗,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,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.在方圆百里之内,设官员立教师,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,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,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,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,使天下人愁苦吗?至于不作大的更改,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,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?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,但可因循旧制,沿用先王的旧制度,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.至于科举的办法,实行了一百年,国家的治乱和盛衰,根本不由此决定.陛下看祖宗的时候,科举的办法,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?言语和文章,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?所得到的人才,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?天下的事,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处理得好?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,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.
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: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,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,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,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,这些都是知其一,不知其二的人.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、重大的事情上,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.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.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,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,而现在治学的人,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,读他们的文章,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;看这些人的相貌,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,这难道真能如此吗?大抵中等人的性情,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.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? 议上,神宗悟曰:“吾固疑此,得轼议,意释然矣.”即日召见,问:“方今政令得失安在?虽朕过失,指陈可也.”对曰:“陛下生知之性,天纵文武,不患不明,不患不勤,不患不断,但患求治太急,听言太广,进人太锐.愿镇以安静,待物之来,然后应之.”神宗悚然曰:“卿三言,朕当熟思之.凡在馆阁,皆当为朕深思治乱,无有所隐.”轼退,言于同列.安石不悦,命权开封府推官,将困之以事.轼决断精敏,声闻益远.会上元敕府市浙灯,且令损价.轼疏言:“陛下岂以灯为悦?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.然百姓不可户晓,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,夺其口体必用之资.此事至小,体则甚大,愿追还前命.”即诏罢之.
【译】 奏议上呈后,神宗觉悟地说:“我本来怀疑这事,得到苏轼的奏议,心里就清楚了.”当天召见他,问道:“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?即使是我的过失,也可以指出来.”苏轼回答说:“陛下性格天生明知,上天赐予文才武功,不用担心不明察,不用担心不勤政,不用担心不决断,只担心治理事务太急躁,听人话语太宽广,进用官员太快速.希望能以安静来治理国家,等待事物的出现,然后加以处理.”神宗震惊地说:“你的三句话,我应当仔细地考虑.凡是在馆阁的人,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的办法,不要有所隐瞒.”苏轼退下,和同僚讲起这些事.王安石不高兴,令他做开封府推官,将用事务来困扰他.苏轼决断精当敏捷,名声传得更远.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,而且命令降低价格.苏轼上疏说:“陛下难道喜欢灯吗?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.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,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,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.这件事极小,而关系很大,希望您能追回成命.”皇帝下诏书免去此举.
时安石创行新法,轼上书论其不便,曰:
臣之所欲言者,三言而已.愿陛下结人心,厚风俗,存纪纲.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,如木之有根,灯之有膏,鱼之有水,农夫之有田,商贾之有财.失之则亡,此理之必然也.自古及今,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,刚果自用而不危者.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.
祖宗以来,治财用者不过三司.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,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,使六七少年,日夜讲求于内,使者四十余辈,分行营干于外.夫制置三司条例司,求利之名也;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,求利之器也.造端宏大,民实惊疑;创法新奇,吏皆惶惑.以万乘之主而言利,以天子之宰而治财,论说百端,喧传万口,然而莫之顾者,徒曰:“我无其事,何恤于人言.”操网罟而入江湖,语人曰“我非渔也”,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.驱鹰犬而赴林薮,语人曰“我非猎也”,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.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,则莫若罢条例司. 今君臣宵旰,几一年矣,而富国之功,茫如捕风,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,祠部度五千余人耳.以此为术,其谁不能?而所行之事,道路皆知其难.汴水浊流,自生民以来,不以种稻.今欲陂而清之,万顷之稻,必用千顷之陂,一岁一淤,三岁而满矣.陛下遂信其说,即使相视地形,所在凿空,访寻水利,妄庸轻剽,率意争言.官司虽知其疏,不敢便行抑退,追集老少,相视可否.若非灼然难行,必须且为兴役.官吏苟且顺从,真谓陛下有意兴作,上糜帑廪,下夺农时.堤防一开,水失故道,虽食议者之肉,何补于民!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?
自古役人,必用乡户.今者徒闻江、浙之间,数郡顾役,而欲措之天下.单丁、女户,盖天民之穷者也,而陛下首欲役之,富有四海,忍不加恤!自杨炎为两税,租调与庸既兼之矣,奈何复欲取庸?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,庸钱不除,差役仍旧,推所从来,则必有任其咎者矣.青苗放钱,自昔有禁.今陛下始立成法,每岁常行.虽云不许抑配,而数世之后,暴君污吏,陛下能保之与?计愿请之户,必皆孤贫不济之人,鞭挞已急,则继之逃亡,不还,则均及邻保,势有必至,异日天下恨之,国史记之,曰“青苗钱自陛下始”,岂不惜哉!且常平之法,可谓至矣.今欲变为青苗,坏彼成此,所丧逾多,亏官害民,虽悔何及!
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,用贾人桑羊之说,买贱卖贵,谓之均输.于时商贾不行,盗贼滋炽,几至于乱.孝昭既立,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,天下归心,遂以无事.不意今日此论复兴.立法之初,其费已厚,纵使薄有所获,而征商之额,所损必多.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,以一牛易五羊.一牛之失,则隐而不言;五羊之获,则指为劳绩.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,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,何以异此?臣窃以为过矣.议者必谓:“民可与乐成,难与虑始.”故陛下坚执不顾,期于必行.此乃战国贪功之人,行险侥幸之说,未及乐成,而怨已起矣.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,此也.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,在道德之浅深,不在乎强与弱;历数之所以长短者,在风俗之薄厚,不在乎富与贫.人主知此,则知所轻重矣.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,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.爱惜风俗,如护元气.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,勇悍之夫可以集事,忠厚近于迂阔,老成初若迟钝.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,知其所得小,而所丧大也.仁祖持法至宽,用人有叙,专务掩覆过失,未尝轻改旧章.考其成功,则曰未至.以言乎用兵,则十出而九败;以言乎府库,则仅足而无余.徒以德泽在人,风俗知义,故升遐之日,天下归仁焉.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,事不振举,乃欲矫之以苛察,齐之以智能,招来新进勇锐之人,以图一切速成之效.未享其利,浇风已成.多开骤进之门,使有意外之得,公卿侍从跬步可图,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,欲望风俗之厚,岂可得哉?近岁朴拙之人愈少,巧进之士益多.惟陛下哀之救之,以简易为法,以清净为心,而民德归厚.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,此也.
祖宗委任台谏,未尝罪一言者.纵有薄责,旋即超升,许以风闻,而无官长.言及乘舆,则天子改容;事关廊庙,则宰相待罪.台谏固未必皆贤,所言亦未必皆是.然须养其锐气,而借之重权者,岂徒然哉?将以折奸臣之萌也.今法令严密,朝廷清明,所谓奸臣,万无此理.然养猫以去鼠,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;畜狗以防盗,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.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,下为子孙万世之防?臣闻长老之谈,皆谓台谏所言,常随天下公议.公议所与,台谏亦与之;公议所击,台谏亦击之.今者物论沸腾,怨讟交至,公议所在,亦知之矣.臣恐自兹以往,习惯成风,尽为执政私人,以致人主孤立,纪纲一废,何事不生!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,此也.
【译】 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,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,说:
我所想说的,三句话而已.请求陛下维系人心,敦厚风俗,保存法纪.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罢了,正像树有根,灯有油,鱼有水,农夫有田,商人有钱.失去了就会灭亡,这是必然的道理.从古到今,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,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.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的不满了.
从祖宗一直以来,管理财政的是三司.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,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,用六七个青年人,日夜在里面讨论研究,又派出四十多人,分头出外办事.那制置三司条例司,是求利的名义;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派出人员,是求利的工具.开创的声势很大,百姓实在惊讶疑虑;创立的法令新奇,差吏都很畏惧疑惑.用皇帝的身份来谋求财利,用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务,人们产生种种议论,万民议论纷纷,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,还说:“我没有这事,何必顾虑别人说.”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,对人说“我不是去捕鱼”,不如丢掉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.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,对人说“我不是去打猎”,不如放掉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.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,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.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,几乎一年了,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绩,还茫然像捕风一样,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,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.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,谁不能做呢?而所实行的事情,路人都知道其困难.汴河的水很混浊,从有人以来,不用来种稻.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,一万顷的稻田,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,一年一淤,三年而陂池就满了.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,即使考察地形,所在之处凿空,寻求水利,狂妄庸人轻浮,随意争相进言.有关部门虽然明了办法不合适,不敢就此斥退,却追集当地老少,去看可否实行.如果不是明显地难于做到,必定姑且兴起工役.官吏们暂且顺从,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,对上浪费国家财物,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.堤坝防线一开,水流离开就有的河道,即使吃了建议者的肉,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!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?
从古以来的役人,一定用乡间的人.现在听说江、浙之间,有几个州雇人代役,而要把这办法施行于天下.单丁户、女户,这是天生百姓中穷苦的人,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,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,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!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,原来的租调与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,怎么又想取力役钱?万一后代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,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,以此追查,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.青苗放钱,以前就禁止.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,每年都照常执行.虽说不许强迫借款,而几代之后,暴君和贪官的出现,陛下能保证得了吗?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,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,用鞭打来催还很急,接着是逃亡,人不回来,就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,这是势所必然的,将来天下人恨这事,国史记载此事,说“青苗钱从陛下开始”,难道不可惜吗!而且常平之法,已经极好了.现在要变为青苗法,破坏那一种确立这一种,所损失的更多,亏损官府危害人民,(到那时)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!
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,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,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,叫作均输.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,盗贼更猖獗,几乎酿成乱事.孝昭登上帝位后,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,天下归心,没有出现乱事.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此论又兴起了.立法之初,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,纵然能稍有收获,而能征收的商税,所受损失必然很多.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,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.失去一头牛,就隐瞒不说;获得五只羊,却指为功劳.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,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,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?我以为是错了.议论的人必然说:“百姓乐于见到成功,却难于开始.”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这种做法,一定要实行下去.这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,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,不等到事情的成功,而怨恨已经起来了.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的原因,就在于这里.
国家存亡的原因,在于道德的深浅,不在于强大和弱小;朝代长短的原因,在于风俗的厚薄,不在于富裕和贫穷.君主如果懂得这些,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.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,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.爱惜风俗,像保护元气一样.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,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,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,老成的人看似迟钝.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的原因,是知道那样做说得少,而所丧失的要多.仁宗执法极为宽大,用人有次序,专求体谅人的过错,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.查考政绩,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.拿用兵来说,十次出兵九次失败;拿府库来说,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.但恩德在人们心中,风俗是普遍知道礼仪,所以逝世的时候,天下人都归心于他的仁德.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,没有振作,就想用苛察来纠正,用智慧能力来整顿,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,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.还没有收到好处,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.开了很多骤然晋升的门,使人有意外的得益,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,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期望,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,难道能得到吗?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,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.请陛下哀怜拯救,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,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,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.我希望陛下淳厚风俗的原因,就在于这里.
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,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.即使小小有所责罚,不久就将其超升,允许他们将所听到的上奏,而不论是涉及什么官长.说到皇帝,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;有关朝廷,那宰相就得等候处理.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贤能,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.但须要养成他们敢于说话的勇气,而给予他们大权,难道是徒然的吗?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.现在法令严密,朝廷清明,所谓有奸臣,当然万万没有这个道理.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,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;养狗是为了防小偷,不可以因为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.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,对下为子孙万代作提防呢?我听到长老的议论,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,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.公议所赞同的,御史谏官也赞同;公议所抨击的,御史谏官也抨击.现在舆论沸腾,各种怨恨的话都有,公议所在,也可以知道了.我恐怕从此以后,习惯成了风气,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,直到君主被孤立,法纪全被废除,(到那时)有什么事情不会出现!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纪的原因,就在于这里.
《宋史·苏轼传》原文及翻译
《宋史·苏轼传》原文及翻译:熙宁四年,会上元敕府市浙灯,且令损价。轼疏言:“陛下岂以灯为悦?此不过以奉二宫注之欢耳。然百姓不可户晓,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,夺其口体必用之资。此事至小,体则甚大,愿追还前命。”即诏罢之。时安石创行新法,轼上书论其不便。安石滋怒,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,轼遂请外,通判杭州。时新政日下,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,民赖以安,徙知密州。司农行手实法,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。轼谓提举官曰:“违制之坐,若自朝廷,谁敢不从?今出于司农,是擅造律也。”提举官惊曰:“公姑徐之。”未几,朝廷知法害民,罢之。徙知徐州。河决曹村,泛于梁山泊,溢于南清河,汇于城下,涨不时泄,城将败,富民争出避水,轼曰:“富民出,民皆动摇,吾谁与守?吾在是,水决不能败城。”驱使复入。轼诣武卫营,呼卒长,曰:“河将害城,事急矣,虽禁军且为我尽力。”卒长曰:“太守犹不避涂潦,吾侪小人,当效命。”率其徒持畚锸以出,筑东南长堤,首起戏马台,尾属于城。雨日夜不止,城不沉者三版。轼庐其上,过家不入,使官吏分堵以守,卒全其城。复请调岁夫,增筑故城为木岸,以虞水之再至。朝廷从之。徙知湖州。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,以诗托讽,庶有补于国。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摭其表语,并媒孽所为诗以为讪谤,逮赴台狱,欲置之死。锻炼久之,不决。神宗独怜之,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。轼与田父野老,相从溪山间,筑室于东坡,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翻译:您收回这个命令。”皇帝于是下诏停办这件事。当时王安石正在创制施行新法,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。王安石很愤怒,让御史谢景温在皇帝面前说苏轼的过失。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,做了杭州通判。这时新的政令一天天下达,苏轼在杭州任上总是利用新法中对百姓有利的内容造福百姓,百姓们因此生活安定,调任密州知州。司农实施手实法,不按时施行的人按违反国家制度判罪。苏轼对提举官说:“违反制度的判罚,如果是出自朝廷,谁敢不听从?如今命令出自司农,这是擅自制定律法。”提举官害怕地说:“请您先不要追究这件事。”不久,朝廷知道这个法令危害百姓利益,于是下令废除了它。调任徐州知州。黄河在曹村决口,泛滥到梁山泊,流入南清河,汇集于徐州城下,水位上涨如不及时排泄,城墙将要被浸坏,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。苏轼说:“富人出去了,百姓都动摇,我和谁守城?我在这里,一定不能让水冲塌城墙。”又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。苏轼到武卫营去,对卒长说:“河水将要冲坏城墙,事情紧急,你们虽是禁军,姑且给我出力。”卒长说:“太守尚且不躲避水患,我等小人,应当效命。”他就率领兵卒拿着畚箕铁锹出去,筑起东南长堤,从戏马台开始,直到城墙。雨日夜下个不停,城墙没有被淹没的仅有三版。苏轼住在堤上,路过家门也不进去,派官吏分段防守,最终保全了这座城。他又请求调发第二年的役人来增筑旧城,又用木头筑堤岸,以防水再来。朝廷同意了他的做法。调任湖州知州,上表谢恩。又因为有些事对百姓不利而不敢说,用诗来讽谏,以求有益于国家。御史李定等摘取他章表中的话,并且引申附会他所作的诗说是诽谤皇上,逮捕进御史台监狱,想置他于死地。罗织罪名很久不能判决。神宗独自怜惜他,把他作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。苏轼与农夫老翁,一起在溪谷山林间生活,在东坡建造房屋,自称“东坡居士。”